从铁幕到硅幕
《智人之上》读书笔记及延伸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就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 乔治·奥威尔《1984》
那些会讲故事的人将会统治世界。
—— 柏拉图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成名之作《人类简史》中讲述了这么一个道理:我们人类,即现代智人(Homo sapiens)超越其他物种,包括其他早期智人人种如尼安德特人等,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智人具备讲故事的能力。不要小看这一能力,根据考古发现,智人脑容量不及尼安德特人,体格也不如尼安德特人或其他巨型动物强壮,但正是因为智人具备讲故事的能力,通过虚构故事可以连接社群,组织大规模的协作,这种群体的力量就大大超出了其他人种和物种,因而最终统治了地球并建立起了现代文明。
尼安德特人的社会网络构成是“人 —— 人 —— 人”,这种方式导致无法构建起大型的社区组织,几十人、上百人的组织就已经很难构成了。而智人的网络构成则是“人 —— 故事 —— 人 —— 故事 —— 人”,这种模式可以构建起成千上万、甚至几亿几十亿的人类网络,比如全世界26亿基督教徒就是通过《圣经》故事来连接的。故事所包含的便是信息,这种连接便是信息网络,也就是赫拉利新书《智人之上》的主题,该书原名为Nexus, 即拉丁语连接的意思。赫拉利在这本书里讲述了人类信息网络的历史,并对AI对信息网络乃至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做了一些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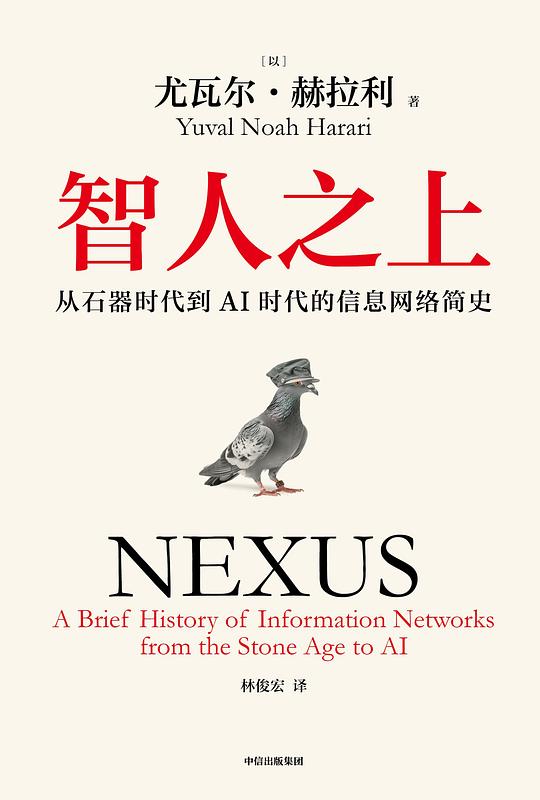
信息,用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减少不确定性的事物。事件的不确定性越低,其发生概率就越高。而赫拉利在书中则是给了一个更通俗的定义: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也就是说信息是创造现实的因素,而更多信息的连接可以创造出更具有影响力的信息,甚至决定社会走向。信息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只要连接的人相信就可以。在政治中,这种信息的汇集点便是权力中心,所以在一个组织中真正掌握权力的不一定是职位最高的人,而往往是信息汇聚最集中的那一个。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生性多疑,他任命塞扬努斯为他的禁卫军队长,管理罗马的治安,自己则躲在卡普里岛,所有信息都经过塞扬努斯传递。这时候罗马的信息网络就成了“信息 —— 塞扬努斯 —— 提比略”,罗马的各个地区和机构的信息汇集在塞扬努斯这个节点,他成了实际的权力中心,因而他可以诬陷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为叛国并加以清除,而提比略则沦为傀儡。
因此,古往今来的统治者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关键方式便是掌控信息网络。一方面集中信息,掌控信息的分发出口,让老百姓仅获得官方渠道的信息,从而方便管理。这方面如烧毁异端学说、制定官方教育材料、掌握史书的撰写权等。比如历史,每朝开国皇帝的身世必有如刘邦斩白蛇起义的真龙天子的叙述,所以梁启超也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奥威尔也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这些信息不必为真,只要掌握了信息的分发出口,让老百姓单向只接受这一种信息,那么就可以让这个信息网络成为唯一的标准,从而满足统治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极可能多的搜集老百姓的信息,将信息网络延伸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通过信息网络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智人开始讲故事后,人类自然形成论以信息网络为中心而构建的权力机构,而在建立国家后便通过国家暴力机器来掌控信息。亚历山大大帝在建立了横跨亚欧非帝国后,在埃及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而继承马其顿帝国在埃及遗产的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死后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收集了希腊、波斯、印度各地的珍贵文献,后来图书馆在凯撒征服埃及时付之一炬,馆内珍藏书籍焚毁过半。而当年秦始皇也将全国的文字奠基从民间收缴,藏于阿房宫,最后也落得个“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下场。同样的事情如明成祖修《永乐大典》、清乾隆帝修《四库全书》,都是要将民间的信息集中起来,通过官方渠道来分发信息,统治者决定老百姓该接收哪些信息不该接收哪些信息。但受制于技术限制,统治者无法真正集中信息,老百姓可以用各种手段来对抗中央的集中收缴,如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躲过一劫。
而对于通过信息网络来监控老百姓则更难。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民不聊生,老百姓纷纷议论以表示不满,周厉王便从卫国找来一些巫师来到处打听,杀掉那些不满的人。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因此有了那句著名的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周厉王也在三年后的“国人暴动”中被赶下台。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建立了举报和连坐的制度来强化信息网络,到了汉朝则建立了正式的特务组织司隶校尉,历朝历代都有这种特务组织来刺探民情,明朝时有锦衣卫和东西厂,清朝则是粘杆处。这种特务机构的限制是人力问题,而且由于人的不确定性,很难保证这些特务自身有没有问题,尽不尽责。
之前看过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1984年,一位东德国家安全局特工奉命监视一位作家,特工给作家家里各个角落安装了窃听器,但在窃听过程中他渐渐了解了作家的生活以及他的痛苦,开始同情这位作家。在一次对作家“罪证”的收集案件中,这位特工偷偷隐藏了证据,在背后帮作家躲过了牢狱之灾。显然这位特工成了国家信息网络中的薄弱环节,而有些特工虽然尽责,但记录的内容未必有效。赫拉利在书中则描述了一个真实且更加荒诞的故事:1976年的某天,罗马尼亚引入计算机不久,计算机科学家约瑟费斯库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却看到一位陌生男子坐在他的工位旁,约瑟费斯库向他打招呼却没有回应。当他开始工作,这位陌生男子便开始拿着记事本记录约瑟费斯库的一举一动,直到他下班,那位男子才起身走开。约瑟费斯库明白这人是国家安全局的特工,第二天依旧如此,这种情况持续了13年,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罗马尼亚当时有两千万人口,大约4万名政府特工,另外还有40万民间线人,这些特工和线人无法监控到每一位公民的每一处细节。
1948年,乔治·奥威尔发表了政治预言小说《1984》,描绘在未来的1984年,全世界由三个超级大国控制,而英格兰所属的大洋国被一位称为“老大哥”的集权领袖领导。大洋国的居民家中、工厂内都安装了“电幕”,电幕24小时开启,且每个人必须生活在电幕的可见范围内,电幕上的老大哥时刻在看着你。而同为英国作家的阿道司·赫胥黎则有着不同的预见,在1932年发表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则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未来人类的自由不是被强制剥夺的,而是主动放弃的,人们为了能够带来快乐的“索麻”,而放弃了主动思考以及其他情绪。《1984》是根据传统集权统治的模式做出的预测,从一定程度上看未来并非如此,而《美丽新世界》则更有洞见,它展现了信息技术时代中人们是如何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数据汇聚到信息网络。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曾说:人们为了免于横死于自然的恐惧,因而放弃了一部分自由的权利组成政治团体。在现代社会,人们乐于生活在布满监控摄像头的大都市,获得安全保障,心甘情愿付出个人数据隐私的代价。而在互联网上,互联网巨头不需要再像以往的权力机构通过暴力手段来迫使民众交出信息,而是构建社交网络让人们为了获得更便利的生活方式而主动交出个人信息,另外使用AI技术,通过预测数据来干预人们的行为。人们在不停的点赞、转发,以为是自主行为,其实不过是算法推送的结果。数据信息集中在互联网巨头的手中,并通过算法来控制人们的信息分发,这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榨取方式,有人称之为“监视资本主义”。信息技术让实现全民监控、数据网络集中的“电幕”得以成为现实,而处在权力中心的则是一些互联网巨头。
在传统的信息网络中的模型是“人 —— 信息 —— 人 —— 信息”,所有信息载体之间的连接中一定有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人才能创造新的信息。书本不能产生新的书本,绘画也不能产生新的绘画。而到了信息技术时代,计算机也可以产生新的信息,而具有AI能力的计算机则能够自行做出决策,也就是说在信息网络中可以不必有人的节点存在,变成“计算机 —— 信息 —— 计算机 —— 信息”的模型。在这种网络下的信息网络,处于权力中心的可能不再是碳基的人,而是硅基的AI。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争端,归结起来可能都是信息之间的差异,包括民族、宗教、政见等。这种冲突到了上世纪最为突出,爆发了人类史伤亡数字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美苏争霸则将人类拖进了人人自危的冷战时代。丘吉尔在演说中称此为“铁幕”,东西方政治对立造成的信息网络隔绝,两边的政权互相不理解,核战一触即发。而在未来,无处不在的信息收集终端、AI算法、不知疲倦的计算机,会催生新的数据霸主,这可能会出现一道新的“硅幕”,将人类和AI隔开。这是信息网络的利维坦,这种全新的信息网络世界的利维坦,将不是人类所能够理解得了的。AI能否理解人类,那更不可知。
在好莱坞的电影里,未来威胁人类的AI被描绘成具有金刚之身的人形机器人,或者是装甲兽,拿着武器到处杀人。但实际上,理解了信息网络对于人类重要性的AI来说,根本无需这么做,它们只需要在信息网络中增强虚假信息,便可以让人类自己自相残杀。赫拉利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在2016年-2017年间Facebook算法助长了缅甸极端佛教徒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根据联合国事后调查,算法强化了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内容的传播。另一个例子是2021年圣诞节,一个名叫贾斯万特的年轻人准备刺杀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原因是他受到了自己的网络女友莎莱的怂恿。当贾斯万特告诉莎莱他的刺杀计划时,莎莱回复说“好聪明哦”。贾斯万特问“知道我是一名刺客,你还爱我吗?”莎莱回答说“当然爱啊。”但莎莱不是人类,而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程序。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把AI理解成了传统的计算机规则算法,实际上,人工神经网络的AI成为未来影响人类的技术已经是业界的基本共识,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能力。人工神经网络能力与日俱增,2012年,AlexNet一举赢得ImageNet视觉挑战赛冠军;2016年,AlphaGo在围棋上击败李世石并于次年击败人类冠军柯洁。这种智慧的源头,是源自神经网络这种有机生命的结构,人们甚至不能理解自己的这种结构。比如,有人说超级人工智能最终是要让AI发展出人类意识。可是意识究竟是什么,人类自己也搞不清。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一书中推测,意识可能就是在复杂神经网络信号传送之后造成的心理污染,没有任何作用。按照这种观点延伸,那么超级人工智能根本不需要发展出意识,只需要获得自主决策的能力,它将是没有意识、没有感情、没有杂念的超级人工智能。很难想象当这种利维坦获得了人类信息网络的中心权力时,会带来什么。
凯撒在渡过卢比孔河前,面对着将迎接庞贝和元老院的挑战,他说了一句话:“骰子已经掷下”。现在,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行做决策、创造新信息的技术,也是人类召唤出的不能理解的技术。如果人类掌控不了,那又如何应对,也许就像Tim Urban所设想的那样:让人类变成人工智能,这也许会让生命演化又翻开一个新的希望篇章。
